夜读九江丨(论语)信 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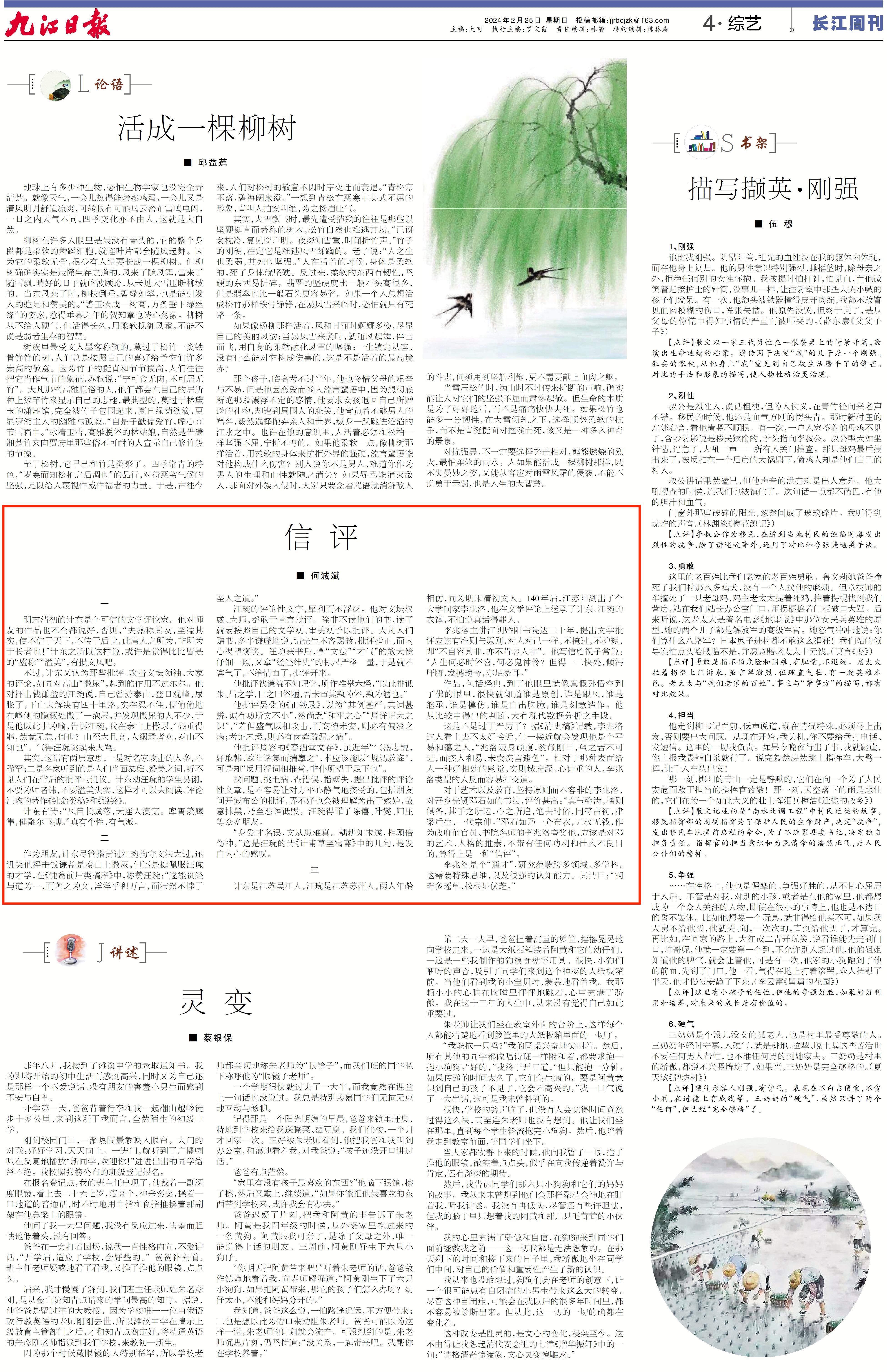
信 评
■ 何诚斌
一
明末清初的计东是个可信的文学评论家。他对师友的作品也不全都说好,否则,“夫盛称其友,至溢其实,使不信于天下,不传于后世,此庸人之所为,非所为于长者也!”计东之所以这样说,或许是觉得比比皆是的“盛称”“溢美”,有损文风吧。
不过,计东又认为那些批评、攻击文坛领袖、大家的评论,如同对高山“撒尿”,起到的作用不过尔尔。他对抨击钱谦益的汪琬说,自己曾游泰山,登日观峰,尿胀了,下山去解决有四十里路,实在忍不住,便偷偷地在峰侧的隐蔽处撒了一泡尿,并发现撒尿的人不少,于是他以此事为喻,告诉汪琬,我在泰山上撒尿,“恐重得罪,然竟无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众,泰山不知也”。气得汪琬跳起来大骂。
其实,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名家攻击的人多,不稀罕;二是名家听到的是人们当面恭维、赞美之词,听不见人们在背后的批评与讥议。计东劝汪琬的学生吴诩,不要为师者讳,不要溢美失实,这样才可以去阅读、评论汪琬的著作《钝翁类稿》和《说铃》。
计东有诗:“风自长城落,天连大漠宽。摩霄羡鹰隼,健翮尔飞搏。”真有个性,有气派。
二
作为朋友,计东尽管指责过汪琬拘守文法太过,还讥笑他抨击钱谦益是泰山上撒尿,但还是挺佩服汪琬的才学,在《钝翁前后类稿序》中,称赞汪琬:“遂能贯经与道为一,而著之为文,洋洋乎积万言,而沛然不悖于圣人之道。”
汪琬的评论性文字,犀利而不浮泛。他对文坛权威、大师,都敢于直言批评。除非不读他们的书,读了就要按照自己的文学观、审美观予以批评。大凡人们赠书,多半谦虚地说,请先生不吝赐教,批评指正,而内心渴望褒奖。汪琬获书后,拿“文法”“才气”的放大镜仔细一照,又拿“经经纬史”的标尺严格一量,于是就不客气了,不给情面了,批评开来。
他批评钱谦益不知理学,所作难攀六经,“以此排诋朱、吕之学,目之曰俗陋,吾未审其孰为俗,孰为陋也。”
他批评吴殳的《正钱录》,以为“其例甚严,其词甚辨,诚有功斯文不小”,然尚乏“和平之心”“周详博大之识”,“若但盛气以相攻击,而商榷未安,则必有偏驳之病;考证未悉,则必有卤莽疏漏之病”。
他批评周容的《春酒堂文存》,虽近年“气盛志锐,好取韩、欧阳诸集而揣摩之”,本应该施以“规切教诲”,可是却“反用浮词相推誉,非仆所望于足下也”。
找问题、挑毛病、查错误、指阙失、提出批评的评论性文章,是不容易让对方平心静气地接受的,包括朋友间开诚布公的批评,弄不好也会被理解为出于嫉妒,故意抹黑,乃至恶语诋毁。汪琬得罪了陈僖、叶燮、归庄等众多朋友。
“身受才名误,文从患难真。耦耕知未遂,相顾倍伤神。”这是汪琬的诗《计甫草至寓斋》中的几句,是发自内心的感叹。
三
计东是江苏吴江人,汪琬是江苏苏州人,两人年龄相仿,同为明末清初文人。140年后,江苏阳湖出了个大学问家李兆洛,他在文学评论上继承了计东、汪琬的衣钵,不怕说真话得罪人。
李兆洛主讲江阴暨阳书院达二十年,提出文学批评应该有准则与原则,对人对己一样,不掩过,不护短,即“不自容其非,亦不肯容人非”。他写信给祝子常说:“人生何必时俗喜,何必鬼神怜?但得一二快处,倾泻肝腑,发摅瑰奇,亦足豪耳。”
作品,包括经典,到了他眼里就像真假孙悟空到了佛的眼里,很快就知道谁是原创,谁是跟风,谁是继承,谁是模仿,谁是自出胸臆,谁是刻意造作。他从比较中得出的判断,大有现代数据分析之手段。
这是不是过于严厉了?据《清史稿》记载,李兆洛这人看上去不太好接近,但一接近就会发现他是个平易和蔼之人,“兆洛短身硕腹,豹颅刚目,望之若不可近,而接人和易,未尝疾言遽色”。相对于那种表面给人一种好相处的感觉,实则城府深、心计重的人,李兆洛类型的人反而容易打交道。
对于艺术以及教育,坚持原则而不容非的李兆洛,对吾乡先贤邓石如的书法,评价甚高:“真气弥满,楷则俱备,其手之所运,心之所追,绝去时俗,同符古初,津梁后生,一代宗仰。”邓石如乃一介布衣,无权无钱,作为政府前官员、书院名师的李兆洛夸奖他,应该是对邓的艺术、人格的推崇,不带有任何功利和什么不良目的,算得上是一种“信评”。
李兆洛是个“通才”,研究范畴跨多领域、多学科。这需要特殊思维,以及很强的认知能力。其诗曰:“涧畔多瑶草,松根足伏芝。”


周刊邮箱:jjrbcjzk@163.com
主编热线:13507060696

编辑:左丹
责编:刘芸
审核:姜月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