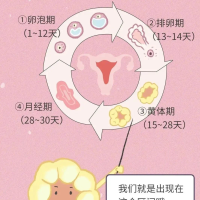乐活岁月丨我为父亲流过的泪
父亲去世13年了,我仍时常想起他。父亲出生于1920年,时值兵荒马乱,祖父母家里本来就十分贫困,父亲的出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温暖和幸福。
父亲的人生十分坎坷。
1930年,祖父母想改变家庭的贫困处境,也想让儿子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他们把10岁的儿子送到村上的私塾读书。父亲天资很好,又勤奋用心,他三年多的时间精读了《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昔时贤文》《孟子》《大学》《中庸》《论语》《琼林》《幼学》等十几册启蒙书籍,且能开篇写文章了。
正当父亲学业日趋长进的时候,因家庭贫困缴不起学费,祖父要求父亲辍学,去跟他学泥工。这一突如其来的闷棍“打”得父亲不知所措,心如刀绞,他缓步走到私塾先生的面前,双膝跪下流着热泪说:“先生,明天我不能来上学了……”
听完父亲这段辛酸的往事,我感到万分凄凉,两行热泪顺着脸庞急流而下,脑子里在深思:父亲如同一棵正在茁壮成长的小树苗,就这样夭折了。
父亲读书成才的美梦破灭了,然而他并不绝望,当我出生之后,他把希望全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家庭再苦他也送我去读书。1959年我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瑞昌县(现瑞昌市)中学,他非常高兴,开学那日凌晨四时多,他挑着一担行李从家里步行出发,陪着我去县中报到。约莫中午,父子俩走到了双板桥客栈。这时,我实在走不动了,就说:“爸爸,在客栈休息一下行吧?”“可以!”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父亲放下行李,立即搬了一条板凳给我坐,又走到店老板面前说了几句话,不大一会,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一碟韭菜炒蛋端上了饭桌,老板说:“小伙子,快来趁热吃吧,这是你父亲给你买的饭菜……”
我向饭桌上望了一眼,心中有些疑惑,怎么只有一碗饭呢?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走上前,说了一声“你赶快趁热吃吧!”中午时刻,我已经是饥肠辘辘,于是,立即端起饭碗大口吃了起来。此时,我看见父亲站在门外,一手端着一杯水,一手拿着什么东西往嘴里啃。我端着饭碗走上前一望,惊呆了:原来他在啃糠粑。这时年仅39岁的父亲正是年富力强的男子汉,靠啃糠粑度日行吗?即刻两行热泪顺着我的脸庞滚落下来。
1968年底,我在江西农垦学校毕业分配工作了。这时正是文革的高峰时期,父亲被列入了“三查”对象。当我在外地听到这消息之后,不知所措。正值寒冬期间,我决定冒着风险探个究竟,除夕,我先到武宁箬溪公社泉口大队港畔村外婆家问个明白。母亲听说我到了外婆家,立即赶来与我会面,她详细地向我讲述了爸爸被列入“三查”对象的具体原因:
1949年春天,村上的保长纠集18个青壮年组织了红黑不明的保安组织,对外就称兄弟会。“三查”中将这个组织定性为“双得险”的反动组织。
当时,父亲被保长以组织兄弟会为名骗到大洼里的山沟里开了这个不明真相的黑组织会议。
父亲从未涉足过政坛,但在那种特殊年月里,很难说清楚自己的清白……
听完母亲陈述之后,我心感不平,决心大胆地试着回故乡与公社大队的“三查”办公室说个清楚明白。当日下午我陪着母亲一路从外婆家回到自己的故乡——瑞昌县(现瑞昌市)南义公社上边村。
晚上9时左右,我的表弟李建明给我母亲送来一个特急情报:大队“三查”办的领导说:“明天大年初一上午要对表兄采取行动,你让表哥今夜就走吧……”
凌晨1时,母亲推开后门,外面漆黑一团,天寒地冻,父亲和槐春叔,妹夫章新榜一起陪着我“外逃避难”,约莫半个时辰,我们一行四人默不作声,既不敢说话,又不敢抽烟,沿着崎岖的小山路前行,连呼吸的声音都压制到最低的限度,生怕惹来意外之灾。
走了一个半小时,我们进入了武宁县地界,这时才松了一口气,可以抽烟说话了。我们再步行两个半小时,过了鹅鸵坂,上搓村,进入新坪畈,陆陆续续听到了附近社员燃放炮竹的声音,到了鸦鹊山脚下,天已经放亮了。
我回头望着他们三人说:“你们辛苦了,回去吧,家里人还望着你们过年呢!”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眼泪就如同开了闸的自来水,哗哗啦啦地往外流……父亲随即双手抱住我嚎啕大哭。
所幸第二年春天,父亲得以平反,生活恢复了平和安宁。从此以后,我也不用再为父亲流泪了。
(易呈学)
本原创内容版权归掌中九江(www.jjcbw.com)所有,未经书面授权谢绝转载。
编辑:柳飘蕙
责编:钟千惠
审核:杨春霞